大概是因為作者覺得,那個時代中外的學術交往相當及時、深入而又誠摯坦率,學術工作者之間的往來主要以學術本身為其目的,而非僅僅是酬酢吹捧或敷衍應付。就以高本漢為例,作者所見高氏論著的中文譯本,「大多都和《左傳真偽考》一樣有著或詳或略的提要和評論,甚至於是對原著錯誤的更正」,以這種態度和方法所進行的翻譯,當然也就超出了單純語言迻譯的價值,本身即構成學術進步的一種載體與手段。
版主按語:
這一代的西方學者對鳩摩羅什之前的漢譯經典用力甚深,成果斐然,如許理和 Erik Zürcher,那體慧 Jan Nattier,左冠明 Stefano Zacchetti ,何理巽 Paul Harrison,魏查理 Charles willemen 等人,他們的著作常有精闢的發揚,但是也有一些重大的疏失(即使是日本學者,例如引田弘道(校註)的《法句經》,(新国訳大蔵経:本縁部4,2000),也有偏差)。
漢語世界的學者,應該較有能力起來評論與對話,但是,從西元1900-2014年以年,漢語世界在此一領域總是不聞不問,更不用談「及時回應、往來以禮」了,這真是「百年孤寂」!孤寂得近乎自閉。
近年來,偶爾見到幾篇對話,例如,紀贇〈《心經》疑偽問題再研究〉一文(2012),回應那體慧 Jan Nattier 《心經:一部中國的偽經?》(The Heart Sūtra:A Chinese Apocryphal Text?), (1992),但是,數量仍然太少。
=====================
2014年6月27日星期五
部落格:
胡適之先生 的世界 The World of Dr. Hu Shih
http://hushihhc.blogspot.tw/2014/06/19271936.html
胡適 〈左傳真偽考的提要與批評〉;高本漢《左傳真偽考》1927、《左傳真偽考及其他》1936
胡適當時如日中天的聲望,卻替一個二十來歲的外國人 (高本漢)的《左傳真偽考》一書,寫了一篇長文〈左傳真偽考的提要與批評〉1927.10.4 上海。
《左傳真偽》的提要與批評
一,著者珂羅倔倫先生 (高本漢)
二,作序的因緣
三,什麼叫作“左傳的真偽”
四,論《左傳》原書是焚書以前之作
五,從方法上證明《左傳》不是魯國人做的
六,關於這一部分的批評
七,下篇的最後兩部分
Zuozhuan zhenweikao ji qita 左傳真偽考及其他. [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 Chinese]
這本小書收錄了戴燕近十年來所寫的有關中國和日本的隨筆、書評和遊記。書中大部分文字與日本的中國學有關,偶爾也涉及別國漢學;還有一部分談論中國的書,有關乎文學史的,也有零星的學術斷想。最有一篇〈枇杷樹〉則詳細記錄了作者丈夫葛兆光先生入院治療眼疾的點點滴滴,讀來情真意切。
《往來以禮》:中外學者應相互批評 
http://www.CRNTT.com 2014-03-21 11:59:24
1926年,瑞典漢學家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舊譯珂羅倔倫)在《哥德堡大學年鑑》上發表了一篇討論《左傳》真偽問題的論文 On the Authenticity and Nature of the Tso Chuan。這篇長文的上半部分評介歷來關於《左傳》真偽問題的各派觀點及其方法論,下半部分以現代語言學的手段分析《左傳》的文法,藉以對這本著名史籍的真偽及作者問題提出新看法。論文發表的第二年,即由陸侃如(1903-1978)口譯、衛聚賢(1898-1990)筆錄,並且經過趙元任(1892-1982)的校訂,題作《論〈左傳〉的真偽及其性質》,發表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月刊》上。不久,新月書店開張,又將這篇論文出版了單行本,改名《左傳真偽考》,這是1927年的10月,上距論文發表僅一年半而已。除了譯文之外,單行本在正文前面還印了胡適的《提要與批評》,書後有衛聚賢的《跋》,全書107頁,中國學者所寫的序跋加起來就占了52頁,而胡、衛兩位皆對高本漢的研究有贊有彈,算得上高質量的論辯往來之作。
這是復旦大學中文系戴燕教授在學術隨筆《往來以禮》中提到的一段學術史往事。「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之所以名為「往來以禮」,大概是因為作者覺得,那個時代中外的學術交往相當及時、深入而又誠摯坦率,學術工作者之間的往來主要以學術本身為其目的,而非僅僅是酬酢吹捧或敷衍應付。就以高本漢為例,作者所見高氏論著的中文譯本,「大多都和《左傳真偽考》一樣有著或詳或略的提要和評論,甚至於是對原著錯誤的更正」,以這種態度和方法所進行的翻譯,當然也就超出了單純語言迻譯的價值,本身即構成學術進步的一種載體與手段。
翻譯如果只是單純地引起此地學者對彼國同行的注意與了解,而沒有學術觀點的甄別、批評與發展,那就是「來而不往,非禮也」。根據作者的描述,高本漢對中文譯者的工作充分尊重,他在《中國音韵學研究》的《著者贈序》中說,三位譯者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全是在這門學問裡極精彩的工作者,對於中國語言史上全有極重要的論著,全給過我許多的益處」,而譯者在書前所寫的《提綱》更其精審中肯,魏建功的書評稱這篇提綱甚至超過《四庫提要》的水準,理應成為「譯書的人和做提要的人」的榜樣。比起法文原書,中文本除了一篇《譯者提綱》而外,還增加了《字體及標點條例》、《名詞表》、《音標對照及說明》、《常引書名表》等幾個部分,對正文所做的潤色及改訂亦不一而足,這都是從讀者和專業研究者的需要出發,而從事的創造性工作。經過此一番動作,《中國音韵學研究》不惟有了一個準確完善的中文譯本,而且等於有了一個修訂升級版。
經過清代數代學者的努力,漢語音韵學已然成為一門相當成熟的專門之學。高本漢以外人而治「小學」,其優長在於挾西方語言學之方法,利用漢語中無比豐富的語言素材,而做綜合性整理性的研究。高本漢對中國本土學者的學術積累充分利用,而他的研究方法與結論也引起了同時中國語言學家的廣泛反響,如傅斯年為《中國音韵學研究》所寫的序中所說,學問之道不限於國界,國人應當「接受此書,一如高本漢先生之接受中土學人之定論也」。這大概就是「往來以禮」的最好說明吧。
再回到《左傳真偽考》。《往來以禮》的作者沒有提到的是,1927年中譯本出版之後,1936年4月商務印書館又出了一個增訂本,題作《左傳真偽考及其他》,除了初版本的所有內容之外,還增加了高本漢的兩篇論文:一是《中國古書的真偽》(原文於1929年發表在斯德哥爾摩的《遠東博物館年刊》上,全文中譯本首次發表於《師大月刊》1933年第2期),二是《書經中的代名詞「厥」字》(原文於1933年發表在《哥德堡大學年鑒》,中譯本首次發表於北京《文學年報》1936年第2期),以及兩篇中國學者接續討論《左傳》問題的論文:馮沅君《論〈左傳〉與〈國語〉的異點》及衛聚賢《讀〈論左傳與國語的異點〉以後》。譯者陸侃如為這個擴充增訂本所寫的序中說,《左傳真偽考》出版以後,引起中國史學界很大的反響,而高本漢也不斷地寄新作給他,所以才有這本新書的誕生。
何以一部討論古籍音韵的著作,會在中國史學界引發如此強烈的影響和持久的往複討論?那原因看起來並不複雜,首先是漢語音韵學有著深厚的積累,中外學者存在討論的共同基礎;二是高著以語言學方法考訂古書真偽,既是其音韵學成就的一次試練,也是古籍辨偽方法的一次推進,對於中國學者而言是以新手段解決舊問題;第三,自從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以來,《左傳》的真偽就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它涉及到中國政治和思想史上一些最重要的主題,所以高本漢的著作才能引發中國學人的極大興趣。
不過,如果再深入一層,也許還有別因素存在。《往來以禮》提到,胡適對《左傳真偽考》的《提要與批評》寫於1927年4月11日,那時胡適在太平洋舟中讀了高本漢的贈書,立刻節譯了出來,並且寫了幾十頁的提要,寄給時在廈門大學的顧頡剛,並且請顧頡剛轉給錢玄同。胡適當月的日記沒有保留下來,不過他寫給顧頡剛的信還在。信中說:「你們看了此文,作何感想?如有地方可以發表,我想大可以發表出來,供大家的討論。標題可用原題。如須發表,最好請你先整理字句,然後付印,能得你和玄同加上討論,然後發表,那就更好了。」最終,這封包含有提要和批評的長信發表在《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第1集的第1期,而這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就是後來鼎鼎大名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前身。
不巧,那時顧頡剛因為魯迅的關係,已經不在廈門大學,而就傅斯年之招,前往廣州了。據顧頡剛在1926年8月寫給錢玄同的信,他在廈門大學本來的計劃是「在這一年中專讀《左傳》、《國語》二書,立起春秋史的骨幹,並將二書並成一書」。不料那年他為人事上的糾紛纏身,成績有限,顧頡剛在回覆胡適的信中說:「現在不但不能做《東壁遺書》的序,恐即侃如所譯之《左傳考》也不能做跋。」這也是顧頡剛、錢玄同沒能參與對高本漢《左傳真偽考》討論的原因。即便如此,在《左傳真偽考》印出單行本以後,胡適曾寄給顧頡剛一册,顧氏還是特別回信指出高本漢論「及」字的錯誤,他對於高本漢的看法是相當重視的。
胡適得到高本漢的贈書,首先想到的是顧頡剛、錢玄同,與當時國內學界的格局密不可分。1926年6月,與《左傳真偽考》英文版的發表幾乎同時,《古史辨》第一册正式出版,立刻就引起了思想界的大風暴。這部著作的主體部分由數十封關於古史辨偽的書信構成,胡適、顧頡剛、錢玄同是三位最主要的作者。胡適對《左傳真偽考》的重視,固然源於他本人對漢語語言學的持久興趣,但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正在蓬勃興起的古史辨運動所引發的考訂偽史風潮。換句話說,在上古典籍辨偽這一點上,高本漢與中國學界產生了共振。
初看上去,這次共振的「點」是在語言學,因為高本漢在發表《左傳真偽考》之前,曾在哥德堡大學開設過《左傳》的研習課程,著眼點就是語言學,而當日中國語言學界也正在急切地吸納西方語言學的方法與技術,正如《往來以禮》所說:「那個年代,中國學界彌漫的與歐美溝通和接軌的熱情,也實在非比尋常。自從《馬氏文通》出版以來,語言學領域便有了越來越強的以西洋為師的習慣,就連最傳統的音韵學,也逐漸同原來的語碼和系統拉開了距離。」不過更進一步說,古史辨運動講求以「科學方法」整理中國古史,雖然延續了清代辨偽學的傳統,但從根本的方法論上來講,同樣是在「以西洋為師」。
後人追慕當年中外學術交流的誠摯和坦率,當然是有感於今天學術溝通的種種亂象。不過也有兩點是該注意的:第一,當年西方的漢學研究以語言學為其出發點,而語言學本身是門技術性很強的學科,一般來說較少受到政治或意識形態的影響(當然在泛政治化時代也難逃羅網);第二,那時中國文史研究儘管正在經歷方法的重大轉換,但從總體的規模和深度上來講,西方漢學仍無法與中國本土學者的研究相比擬。高本漢相當急切地想讓中國同行了解他的研究成果,中國學者毫無障礙地將西方同行的研究納入學術積累,都有上述兩個前提做鋪墊。如今,這兩個前提都不再理所當然,研究理念的分化、政治立場的壁立、民族情緒的干擾,種種觀念的、意氣的、利益的因素都摻雜期間,中外學者各其面臨的問題,各有其複雜的語境,道術已為天下裂的時代,學者間的交往還能往來以禮嗎?
去年,《往來以禮》與作者的其他近二十篇學術隨筆一道收進了同名的作品集,在中華書局出版。作者的學術背景與日本較為密切,所以書中大部分的內容都與日本的中國學研究有關,許多內容並一定為中國文史學界所熟悉。「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理解是交流的第一步,而準確深入的認知則是理解的前提,這部小書的重點並不在於提供關於域外中國研究者的具體知識,卻是開在界牆上的一扇窗,讓人窺見原來別人家的花園也同樣豐富而精彩。
(來源:《中華讀書報》)
=================================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51135057/
暫時注銷 2014-04-07 01:14:10
1927年10月,新月書店出版了陸侃如翻譯的高本漢(舊譯「珂羅倔倫」)著《左傳真偽考》(胡適曾譯作《論〈左傳〉之可信及其性質》),這部以比較文法的方法來證明《左傳》非魯人所寫的著作,最初在瑞典發表,不過是一年半以前的事情,高本漢此前曾在瑞典哥德堡大學開設過《春秋》、《左傳》的研習課程。
那個時代的中國學者,對歐美漢學界的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非常在意,不亞於我們今天對海外學術動向的關注和了解。
2010年春季,當我從香港的圖書館借出《左傳真偽考》的中譯本,感觸最深的還不是這一點,讓我最感興趣的還是薄薄107頁的這本書,除去正文,前面有胡適的《提要與批評》,整整40頁,後面有衛聚賢的《跋》,也占了12頁。胡適的《提要與批評》,在早年的《胡適文存》和新編的《胡適全集》裡都很容易見到,但是如果沒有見到《左傳真偽考》的這個中譯本,不能對這篇《提要與批評》的篇幅,尤其是它與高本漢的正文之比有一個直觀印象,還是难以想象胡適曾經是花了怎样的功夫去細读作者送给他的這本書,也很難聯想到這種舊式「提要」的寫法,在現代學術史上有過怎樣一段「死灰復燃」、神威再現的歷史。
從陸侃如的《譯者引言》和衛聚賢的《跋》裡,我們可以知道《左傳真偽考》的原本是趙元任從作者處獲贈,轉送給李濟之,再輾轉到衛聚賢手裡的。此時的衛聚賢,因為用統計學的方法考得《左傳》的成書年代以及作者乃孔門弟子子夏,受到梁啟超的表揚,已經成了嶄露頭角的《左傳》專家。拿到高本漢的這本書,他馬上迫不及待地請了自己清華研究院的同學陸侃如為他講述書的内容,而陸侃如因為出版過《屈原》、《宋玉》兩本書,這時也被視為學界的後起之秀。於是,陸侃如口譯,衛聚賢筆錄,「全書共六十餘西頁,竭兩日夜之力始竣事」。在《跋》裡,衛聚賢一面表達著自己對高本漢由衷的贊佩之情,稱他是以文法考證《左傳》真偽的「第一人」。然而另一方面,對於書中的結論,他也毫不客氣地提出異議。他說文法的差異,不光由地域造成,應該也有時間的關係,他也不同意高本漢對於《左傳》編纂之年的考定。
現在我們講陸侃如、衛聚賢這一代民國以後國内培養的學者、清華研究院畢業的學生,有時候會過分強調他們的所謂「國學」功底,而忽略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起碼在他們成長的初期,海内外的學術同行之間還是可以進行正常交流的。有一個暢通的交流渠道,有一個寬鬆的交往環境,這其實是這一代人在學問上能够起點較高的原因之一。作為年長一輩的學者,胡適在這方面的貢獻,當然也已經眾所周知。這篇《提要與批評》的初稿,就是胡適半年前在太平洋舟上讀了高本漢的贈書以後,本來要寫給「疑古」的顧頡剛和錢玄同,供他們討論用的,所以它後來也發表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和《古史辨》的第五輯上,它的修訂稿,就作了《左傳真偽考》的陸譯本長序。
提要的編寫,在中國,至少始於一千多年前。近代以來,人們往往把清朝四庫館臣編寫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看成「提要」的一種標準寫法,認為它可以用來「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即便放在這樣一個傳統裡面,胡適的這篇《提要與批評》也算得名副其實。它共有七節——著者珂羅倔倫先生、序的因緣、什麼叫做「左傳的真偽」、論《左傳》原書是焚書以前之作、從文法上證明《左傳》不是魯國人做的、關於這一部分的批評、下篇的最後兩部分——把作者、書以及自己的評斷,交代得清清楚楚、本本分分。
學術史上總有一些經典,值得後人揣摩和效仿,胡適的這篇《提要與批評》,我想也可以列入其中。作為提要,它完整地概括了高本漢書的内容,不走樣,無遺漏,同時揭示它的方法、檢驗它的證據及結論,絲絲入扣,條理清晰,最後將它置於中國乃至國際學界的相關研究脈絡中來做評價,態度誠懇,意見平實。以我自己的淺見,寫出這樣的提要,看似容易,實際並不輕鬆。專業知識的累積、學術行情的掌握、精讀文本的耐心,少一樣都不能成立。而胡適的這一句話:「我們只要能破除主觀的成見,多求客觀的證據,肯跟著證據走,終有東海西海互相印證的一日的。」在我看來,又是既能表現他個人在學術上的包容心,也能傳達那個時代的中國學者襟懷開放却又不失自信的心理。
胡適當日以金針度人的熱忱推薦高本漢的著作,自然有一個屬於他自己的情結,那便是對西式文法的推崇。早在留學期間,胡適就寫過〈《詩》三百篇言字解〉(1913)的文章,嘗試「以新文法讀吾國舊籍」,他還希望凡通曉歐西文法的年輕學人,今後都能「以西方文法施諸吾國古籍」並能總結出一套「成文之法」,使「後之學子能以文法讀書,以文法作文」,而令我「神州之古學」終有「昌大之一日」,由此,他對高本漢的分析文法也就相當看重。這位瑞典漢學家能和自己一樣做著「開山的工作」,讓他不免有了惺惺相惜之心。
然而有趣的是,盡管口口聲聲贊揚高本漢「有開路的大功」,胡適也並沒有忘記《左傳》研究的中國語境,他對高本漢的批評,也大多來自這個語境。他有一個意見,說的就是高本漢對中國學界的成果缺乏了解:考訂《左傳》真偽,却沒有讀過劉逢祿、康有為的相關研究。問題要從德國的佛朗克(Otto Franke)那兒轉引來,可這個佛朗克又是連崔適的《史記探原》也沒讀過的,單憑對康有為之為政客的人格的不信任,就懷疑他有關《左傳》的論述。這種考證的方法本來就不很科學。
瑞典學者馬悦然為高本漢寫過一本傳記,去年這部傳記也有了中文本,名字就叫《我的老師高本漢——一位學者的肖像》。在這部傳記裡,高本漢這位二十世紀最著名的瑞典漢學家,與他的研究對象中國,在現實世界,似乎從來就沒有建立起多麼親密的關係。不過,這並沒有妨礙他成為瑞典以及歐洲漢學界的裡程碑式的人物,也沒有妨礙他在中國語言學界不止一代人中間留下深刻的印記。
出生在瑞典的高本漢,一生中只有兩次踏上中國的土地,盡管從大學時代起,做一名從事日語、漢語工作的教授,就是他最大的心願。那正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盛行歐洲的年代,梵語研究給整個語言學界帶來巨大的震撼,也影響著高本漢對自己學術方向的選擇。在聖彼得堡學習漢語期間,他更得知歐洲漢學界目前最不能令人滿意的,就是語言學、語音學方面人才的短缺。1910年,接受過相當正規的瑞典方言調查訓練的高本漢先是到了上海,然後抵達太原。在接下來的大約一年半時間裡,他一面學習漢語,一面對山西、陝西、甘肅、河南等地的方言展開調查,當親眼目睹了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之後,返回瑞典。
在馬悦然寫的傳記書裡,最有趣、也最珍貴的,是它收錄的大量高本漢寫給家人和師友的信件,這些私人間的通信,對我們探尋一個偉大學者學問之外的内心世界,有極大的幫助。
高本漢曾經從太原寫信給他的女友說:「當你來到這裡的時候,完全不像大家說的那樣,一下子就會叫與我們的文化不同的東西搞得目瞪口呆。正好相反,這裡的物質文化與我們的極為近似感到很遺憾。」(111頁)這位躊躇滿志的未來漢學家,對相距遥遠的中國,竟是沒有一絲一毫初來乍到的陌生感和隔膜感。大半年過後,在另一封寄給女友的信裡,他又寫道:「今天孟子有一小段話讓我覺得理性和新鮮。如你所知,在西方國家人們一直在討論,人的本性天生就是善的,還是像基督教說的是後天繼承下來的。孟子說:『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我覺得此話非常睿智。」(113頁)雖然此前不久,他才向女友描述過另外一番極其現實、冷酷的情形:義和團運動以後,中國被迫向西方列強讓步,「天知道,目前漢學通掙得了多少錢。但是可以預見,中國將再次自食其果。毫無疑問,受到利益驅動的國家都會來,把它完全瓜分掉,就像過去的波蘭一樣,那時候我的股票會成千倍增值。那時候英國和美國、法國和德國都會需要大量高素質的中文教師」(79頁)。可是對於古典的中國文化,高本漢却似乎抱了那麼一點點奇怪的溫情。也許就是這一點點溫情,彷彿潛流似的,成為他開闢漢學新領域的一種内在動力?
二十世紀初的聖彼得堡和巴黎都是歐洲漢學的中心。從太原歸來的高本漢,隋即去了有沙畹、伯希和、馬伯樂的巴黎。在那裡,他一面痛感著漢學界在語言學研究上的落後以及由此造成的與世界學術潮流的差距,一面費盡心機地四處搜求漢語方言,他還嘗試利用傳統韵書來構擬中國的中古音。在這一階段,他選擇了將歷史語音學作為自己研究的方向,這是因為他敏銳地發現,歐洲學界「不少樂觀的先生試圖把漢語與其他不同的亞洲語言聯繫在一起」。他對此十分不滿,並指出某裝幀豪華的英國書籍「試圖確立蘇美爾語與漢語有血緣關係,其根據是大批現代漢語方言的讀音」,其危險性正不亞於冰面上行走;正確的方法,他認為是要先搞清楚漢語本身的歷史,再考察漢語與其他語言像暹羅語、泰語、藏緬語等等的關係,然後,「才有可能從總體上考慮亞洲居民和他們的語言問題」(《漢學語言學的任務及方法》,147頁)。
堅持漢語語音在歷史上曾經有過變化,不能說今天的漢語方言就與古代漢語完全等同。高本漢的這一觀點,與明清以來陳第、顧炎武、戴震、王念孫等音韵學家的看法不謀而合,這也是「繼承了這一批明清時代音韵學家學說」的現代中國音韵學者為什麼能够接受他的一個重要原因。
1915年,博士一畢業即成為烏普薩拉大學副教授的高本漢,在他第一次課上講授中文的特性,就結合了瑞典語的特徵,解釋中文「也有詞尾的變化」。在此後數十年的漢學研究與教學生涯中,除了1922年有半年訪日,其間也有幾天路過上海,其餘的差不多所有時間,高本漢都是面向歐洲學界或者瑞典聽眾的。在傳記書中,馬悦然多次引述同時代人對高本漢的一個評價,稱他的「普及性科學講座」廣受歡迎、貢獻極大。究其原因,這大概就是因為自年輕時起,高本漢的理想已經非常宏大,他沒有想過只做一個關起門來不問世事的專業學者。從太原寫給女友的信中,他就宣示過:「如果誰在一個國家想建立起一門學科,如我在瑞典想做的,書呆子是辦不成的。與其花十年工夫寫十五本内容翔實的書,不如先辦一個科學性的漢學雜誌,再為它購置設備建立一個中文印刷廠,在烏普薩拉或斯德哥爾摩建一個中國博物館,舉辦多種報告會,掀起一股東方熱潮以及在烏普薩拉大學招收學生。」(75頁)為了實現這些偉大的計劃,開創一個新的漢學事業,他當然不能困守書齋、足不出户。專業方面的成績固然重要,但是他也非常清楚,只有向大眾普及,喚起一般人的興趣,才能獲得更多的資源和更大的支持。
當高本漢發願要在烏普薩拉建立一門新學科的那些年,中國學界包括語言學界也在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王力後來總結1949年以前的中國語言學,說它「始終是以學習西洋語言學為目的」(《中國語言學史》,173頁),在這些被學習、追隨的對象當中,有一個頻繁出現的名字,就是高本漢。早在1922年,聽到高本漢會去北京的消息,趙元任便從美國寫信向黎錦熙急迫地打聽:「這人對於音韵沿革似乎很有研究,你們有誰同他談過沒有?」(《討論國音字母的兩封信》,《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26頁)
趁著在香港訪問、便於找書,我陸陸續續又翻閱了高本漢的其他幾種中文版論著,有王靜如翻譯的《中國古音(切韵)之系統及其演變》(1930)的論文,有張世祿翻譯的《中國語與中國文》(1931)和賀昌群翻譯的《中國語言學研究》(1934)著作,有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聯袂翻譯的《中國音韵學研究》(1940),還有台灣出版的杜其容翻譯的《中國語之性質及其歷史》(1963)和張洪年翻譯的《中國聲韵學大綱》(1972),等等。這裡面,像《中國語與中國文》就是寫給大學預科生的講演稿,它談到中國語,也談到中國文化,因為語言到底是和文化相關聯的。它說:中國的文言是一種書寫的世界語,今天北京下一道命令,各地方都能讀懂,要是廣東音,其他地方人就不一定懂,所以文言是保證政治上大一統的工具,「中國人一旦把這種文字廢棄了,就是把中國文化實在的基礎降伏於他人了」(50頁)。它又說:「中國文字是真正的一種中國精神創造力的產品,並不像西洋文字是由古代遠方的異族借得來的。中國地方對文字特别的敬愛,這種又是西洋人所不能理會的。」(84頁)從文化入手,那植根在不同於西洋文化中的特殊文化裡的漢語,就會變得容易理解吧。所以張世祿在為該書撰寫的《導言》中,稱它的「文辭和學理都很淺顯。但是把中國語文上種種重要問題,都已經給予讀者以確切明瞭的觀念」。
在《中國語之性質及其歷史》一書中,高本漢還曾直言:「我們期望從語言中,即便是極簡單地,認識並了解一點中國人的心境。」(9頁)這位並沒有在中國停留多少時間的漢學家,於他純粹的專業研究背後,原來也隱藏了一份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好奇與關心。二十世紀初,海外漢學家對中國文化的這種關心,尤其是他們借助自己的文化背景而對中國文化所做的審視和描述,對中國人來說也相當重要,變成了中國人觀看自己的一面鏡子。因此,像高本漢這一類對於中國語言特徵的概括性的分析和總結,包括運用在這種分析和總結中的產生自歐洲的語言學理論,都轉而為它的中國讀者提供了一個新的自我,同時也提供了新的自我認知的工具。這個新工具,一方面把中國的漢語同印歐語、阿爾泰語等世界上的其他語種聯繫到一起;另一方面,又把漢語中的文言同方言區分開來。把漢語同曾經共為漢字文化圈的日語、韓語、越南語等等區分開來,這樣,漢語也就處在了一個可供比較的新的語言空間。因此,被馬悦然稱作「高水平的科普作品」的這些高本漢的著作,對於以歷史比較語言學為主流的歐洲來說,是一個新世界的展現,帶來新的學術資源。同樣,對於變革中的中國和中國學界,它們也不啻為一個新世界、一種新資源。
這就是為什麼胡適在為《左傳真偽考》撰寫的《提要與批評》中,給予高本漢那麼高的評價,說:「中國向來研究古今聲韵沿革的學者,自陳第、顧炎武以至章炳麟,都只在故紙堆裡尋線索,故勞力多而成功少……珂先生研究中國的古音,充分地参考各地的方言,從吳語、閩語、粤語以至於日本安南所保存的中國古音,故他的《中文解析字典》詳列每一字的古今音讀,可算是上集三百年古音研究之大成,而下開後來無窮學者的新門徑。」
1920-1930年代,高本漢的著作被翻譯得既多且快,這位一心要在瑞典或說歐洲漢學界建功立業的學者,在中國好像也遇到了不少知音。這當然與他本人具有強烈的與中國學界溝通的欲望並非沒有關係。他大概總是能把自己的最新論著,送到胡適、趙元任、丁文江、錢玄同、楊樹達這樣一些與歐美學界關係密切或是本來在學術上就有新變想法的人手裡。不過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那個年代,中國學界彌漫的與歐美溝通和接軌的熱情,也實在非比尋常。自從《馬氏文通》出版以來,語言學領域便有了越來越強的以西洋為師的習慣,就連最傳統的音韵學,也逐漸同原來的語碼和系統拉開了距離。
高本漢在這一時期,是自覺不自覺地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的。今天,從魏建功給《中國音韵學研究》中文版寫的一篇書評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當高本漢把他的博士論文送給錢玄同,錢玄同直接就「從原書裡把高氏的《廣韵》韵類構擬的音值抽錄出來和國音系統一同親自手寫油印,在北京大學講,自然又加了他自己的意見討論過一番」(魏建功《中國音韵學研究——一部影響現代中國語文學的著作的譯本讀後記》,《魏建功文集》貳,468頁)。而在清華研究院開辦之初,趙元任講語音學,也是不遺餘力地推介高本漢的學說,在《現代吳語的研究·序言》中,他表揚高本漢是「研究中國語言最詳細又最多的」一位音韵學家,稱其「所得的材料可以够使他考定隋唐時代的古音的大概」(趙新娜、黄培雲編《趙元任年谱》,146頁)。前輩學者為之鼓吹、推動,一二十年功夫,便有了不俗的成績。到1935年王力出版他的《漢語音韵學》教材,便自言「差不多是無批判地接受了他的學說」(王力《漢語音韵學》1956年《新版自序》)。賀昌群在為高本漢《中國語言學研究》中譯本寫的《譯者贅言》裡,也很明白地談道:「高氏的結論,我國學者不少接受的,在歐洲則惟馬伯樂常與之處於對立的地位」;「現在國内幾個明敏的語言音韵學者之所以能表現相當的成就,未始非有借於高氏之力。」
不知是偶然抑或事實如此,我所見高本漢論著的一些中文譯本,大多都和《左傳真偽考》一樣有著或詳或略的提要和評論,甚至於是對原著錯誤的更正。像上述王靜如翻譯發表在史語所集刊上的那篇文章,就是經過了譯者修改,包括改正了高本漢原來擬的北平音標的。還有張世祿翻譯的《中國語與中國文》,前面也有一篇非常詳盡的譯者《導言》。當年翻譯出版學術著作,是否都要經過這麼一道程序?還是語言學這一行自有它的特殊要求?直到很多年後,杜其榮在他翻譯的《中國語之性質及其歷史》一書裡,仍是增加了一百二十多條注釋,或補充資料,或提供訓釋,或辨正訛誤,其中不乏援引中國學者的意見以糾正原書偏差的;全書之末,又附有周法高的兩篇文章,大概是用來替代對作者的介紹和評論,而周法高的文章,就指出了高本漢受西方語言學影響、過分拿中國語比附印歐語的問題。
語言學上,我是一竅不通的外行,三十年前受教於周祖謨先生學到的一點音韵學入門知識,也都幾乎忘得乾乾淨淨。只是讀到如此認真周詳的翻譯、如此體現專業水準的提要和評論,受益匪淺,心中便有十二分的敬佩。學術翻譯的目的,應該就是這樣,主要為了給更多的人參與對話、討論和批評提供一個平台,而不僅僅是在表達一份仰慕之情,不是一種榮譽性的事業。
在這些譯本裡頭,最有分量、最堪稱經典的當然要數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翻譯的《中國音韵學研究》。這部以高本漢博士論文為主體的著作,早已為歐美學界矚目,也為中國學者留意。用羅常培的話說,這部書既是集西方的中國音韵學研究之大成,在中國,也可以充當一部空前的「音韵學通論」(羅常培《介紹高本漢的中國音韵學研究》,轉引自張靜河《瑞典漢學史》,124頁)。李方桂曾回憶道,1926年他在芝加哥大學跟愛德華·薩皮爾(Edward Sapire,「薩皮爾」又作「薩佩爾」、「薩丕爾」)讀書時,這位著名的語言學家就建議他要去看此書(徐櫻《我與方桂五十年》,23頁)。而趙元任1924年訪問瑞典的時候,也已經與略帶山西口音的這位漢學家談到了要翻譯此書的事情。四年後,他不但獲授權翻譯,還被委托重編全書(《譯者序》,7頁;趙新那、黄培雲《趙元任年谱》,151頁)。
翻譯出版的過程和細節,所經歷時代的磨難、人事的變遷,合五人之力、積數年之功,在傅斯年為該書寫的《序》和三位譯者寫的《譯者序》中都一一交代。傅斯年的《序》,清楚展現出這一代學者的學術追求遠遠跨越了國境,所以他也把高本漢「具承前啟後之大力量,而開漢學進展上之一大關鍵」的如此高的成就,歸因於其能「綜合西方學人方音研究之方法與我國歷來相傳反切等韵之學」。他並且由此倡導「學問之道不限國界,誠欲後來居上,理無故步自封」,要求「國人之接受此書,一如高本漢先生之接受中土學人之定論也」。
中文本的《中國音韵學研究》,比照法文原書,增加了《譯者提綱》、《字體及標點條例》、《名詞表》、《音標對照及說明》、《常引書名表》等幾個部分,魏建功在上述書評裡說這些都是讀者「最需要的」,他尤其稱讚《譯者提綱》寫得好,說:「這篇比從前《四庫提要》更其精覈公平的提綱是值得給譯書的人和做提要的人做榜樣的!」而馬悦然在他寫的傳記書裡,也談到過「該書的優秀譯文比法文原著更容易理解」(205頁),例如中譯本將原書的瑞典音標改成通行的國際音標,就大大方便於人。不用說,三位譯者花費許多心思改正原著中的疏漏和錯誤,也令中譯本比原著更加可靠。
面對煥然一新的譯本,有意思的是,高本漢自己也感動不已,他在《著者贈序》中給了翻譯者極高的評價。他說:三位譯者「全是在這門學問裡極精彩的工作者,對於中國語言史上全有極重要的論著,全給過我許多的益處,他們三位先生在這部書上犧牲了這麼多寶貴的光陰,使我少年時代生的這個小孩子能够在它的本鄉裡得到一條新生命——這件事是使我非常感動的。」他因此誠懇向幾位中國學者致謝,說:「自從中國新起了一輩學者以來,一部像這樣的書,裡頭有好些地方就變成不能用的成說,要想把它譯成漢文,事先非得徹底的修改一番不可……現在好了,借著我這幾位翻譯先生的大力,這部書不但譯成了極其流暢極其真切的漢文,並且内容上的修改潤色也承他們的好意同時都做到了。」經此一事,他對漢學領域的新變化也愈增感慨:「中國新興的一班學者,他們的才力學識比得上清代的大師如顧炎武、段玉裁、王念孫、俞樾、孫詒讓、吳大澂,同時又能充分運用近代文史語言學的新工具」,「一個西洋人怎麼能妄想跟他們競爭哪?」他以為,一個西洋人,現在只能够「選擇一小部分,作深徹的研究,求適度的貢獻而已。這樣,他對於他所敬愛的一個國家,一種民族,一系文化,或者還可以效些許的勞力」。
《中國音韵學研究》,按照高本漢自己的想法,原本是將「瑞典的方法」移植於中國音韵學的研究,但是,這樣一部以瑞典方法、寫給瑞典讀者的著作,現在却變成了由中國學者參與、合作完成的一個新成果,就像魏建功在上述書評中給出的結論:「這部譯本毋寧說是新中國音韵學者的集體著作。」(《魏建功文集》貳,470頁)這樣的一個結果,自然靠的是中國學者基於強烈主體意識和責任感的積極投入,却也根本離不開高本漢為人的謙遜和治學的公允。在後來出版的《中國聲韵學大綱》一書中,高本漢也還談到過:「這許多年間,我對自己起初的說法,曾作過不少的補充和修改」,其中有的就是「受了同行其他學者的影響,像馬伯樂、李方桂、趙元任及羅常培,便是其中主要的幾位。」(張洪年譯,1頁)
1930年,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邀請高本漢參加他在居延發現的漢簡的整理工作,高本漢回信寫道:我不是最佳人選,雖然在語言學領域,「我確信,我像其他歐洲人(伯希和除外,可能還有馬伯樂)一樣優秀」;但在文字鑑定方面,我却「無法以任何形式與某位優秀的中國文字學家相比」。他建議斯文·赫定不如就在北京找羅振玉或其他人合作,以免重蹈沙畹的覆辙:「曾經鑑定斯坦因第一批和第二批文物的沙畹有過很糟糕的助手,因此他偉大的作品變成了他最難堪的事;羅振玉不得不徹底重新鑑别。沙畹對草書的鑑别能力不錯,但是他沒有著名的蔡元培的幫助一輩子也搞不清楚——恰巧蔡元培當時在萊比錫。」(馬悦然《我的老師高本漢》,172頁)這個一輩子只在中國住了一年半的漢學家,對他的中國同行,却表現出這樣坦誠的完全的信賴,沒有一點猶豫。
我是沒有能力,也無意於評說高本漢的學問以及他在中國學界的影響的。在香港的這個春季與隨之而來上海的酷熱夏天,縈繞心頭的,其實一直是那個年代海内外學術交往的方式,那種互相學習、商討而又互相信任的誠摯坦率的方式,多少讓人感動和懷戀!它是否能像那個時代的學術一樣延續下來,成為我們的一種傳統、一種典範?
2010年8月21日初稿、9月2日定稿於光華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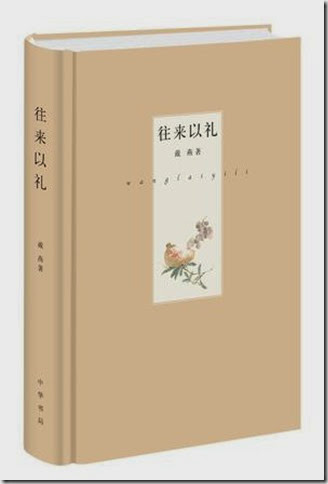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